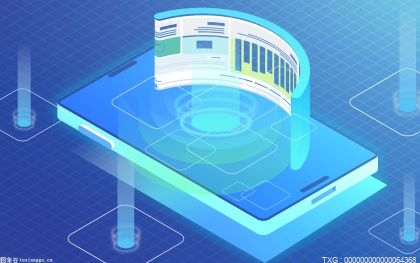北京人爱鸟,是出了名的。每天,带上自家的鸟出门遛一遛,是许多老北京人雷打不动的必修课。在作家的笔下,他们被称作“鸟人”,鸟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。而近年来,不少爱鸟人士开始将注意力从“笼中鸟”转向“丛林鸟”,他们也被视为新一代“鸟人”。
郭耕:这个照片很特殊,1999年国内第一次观鸟大赛,我作为唯一的中国队(代表)上台发言。
郭耕和动物打交道已近四十年,用他的话说,动物保护工作不仅是一种职业,更是他的事业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郭耕:什么是事业和职业?就是我想上班,那就是事业。如果说明天我得上班,那就是职业。
郭耕:到田里,远方“呱呱呱”全是叫的,一看地上田头全是一种叫豆雁的鸟。我就拿着望远镜扫。突然就不动了,我说好像大鸨在这呢。大家都掉转“枪口”,往那找,一看真是大鸨。
东方大鸨是一种极难被观测到的珍稀物种,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全球数量已不足两千只,甚至被认为是“鸟中的大熊猫”。但与大熊猫不同的是,鸟类会自由地迁徙,甚至不经意间出现在人们的身边。
快速的城市发展中,人类挤占了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土地、空间和资源。今年6月,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,“加强自然保护地管理,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”。全市将在部分有条件的绿隔公园建设20处自然带,促进人工林向近自然林转变,为野生动物保留栖息空间。并在“十四五”期间,每年建设120处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区,为小动物营造栖息地。
周彩贤:因为现在我们的基底有了,据我们初步调查,我们的物种大概在6000种以上,如何把它保护好,这其实就是我们园林绿化部门下一步一个宏大的命题。
没有多样的生态系统,完整的生物链条和生物廊道,北京目前的“绿”或许只会是短暂的“绿色荒漠”。北京这样人口急剧密集的超大城市,真的有可能让“绿”活起来,重新成为自然化城市吗?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,“万物共生”的愿景能否实现呢?
“适得其反”的生态保护
羿健和马德成,都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成员,他们口中的它,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鸨。2017年,有观鸟爱好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鸨的踪迹,也就是从那时起,每年冬天,他们都要花上将近一半的时间,守在这里。
大鸨以草籽和谷物为食,眼前这块对人来说并不起眼的土地,对大鸨而言却是完美的越冬天堂。事实上,全球共有八大候鸟迁徙通道,其中北京处于“东亚—澳大利亚”迁徙路线上,每年过境南迁或北迁的候鸟、旅鸟达300多种,数量超过百万。经过几年持续地观测记录,羿健和马德成欣喜地发现,这里已经成为几只大鸨稳定的越冬地,而且除了几张老面孔,队伍还在不断壮大,去年最多的时候达到五只。
郭耕:我觉得这是一个典范,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。农民种地该种还种,但是冬天撂荒了,正好这些鸟到这来越冬。你唯一做的事就是不要去打扰。这几十年来我得出一个经验,保护的关键不是把动物给关起来,而是把人给管起来。
为了更好地保护大鸨,马德成和羿健他们专门起草了大鸨拍摄行为指南,并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。
如今,这个队伍已经发展壮大到将近200人。每年这个时候,他们都会自发地排班,早上8点上岗,下午5点下岗,默默地帮大鸨解决各种问题。
今年,北京市启动了“揭网见绿”新举措,通过简易绿化为荒地“美颜”,既防止了扬尘,又能实现在低维护条件下的区域生态功能。这项本意是改善生态的举措,却在不经意间改变了生态。对于大鸨来说,它们刚刚对这片越冬地适应甚至依赖,现在不得不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改变。
吕植:从人的眼光来看,这个地方乱七八糟,但为什么他们从2015年开始观察,有266种鸟,包括八种一级保护动物在这生活,动物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
吕植,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及生态研究中心教授,也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创始人。早年,她主要从事大熊猫研究和保护,有人称她是“与野生大熊猫最亲近的人”。而身边校园里丰富的动植物,则让她开始关注城市的自然生态。
2008年,在绿色奥运的大背景下,奥森公园摒弃了传统的“公园为人服务”的设计理念,提出仿自然山野的建设标准,同年,53万株近100种乔木、80余种灌木和100余种地被植物,按照生物多样性组成了奥森的自然林系统,公园绿化覆盖率更达到了95%以上。其中,为了净化公园的水质,种植了6万多平方米的芦苇。如今,这片湿地空间,早已成为了动物的乐园。
王军:咱们的芦苇,就是给东方大尾鹰、鸦雀,它们喜欢在这种芦苇里面活动,它就要吃芦苇秆子里的小虫,它除了藏身还要觅食。还有秧鸡什么的,都会依赖于这个环境。
在过去很多年间,为了不使芦苇破坏奥森的水质,同时为了冬天防火,每年11月,公园就会把所有的芦苇都割掉。学习园林出身的王军,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片芦苇,对动物有着如此大的作用。2017年,北京市生物多样性策略研究工作启动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建议王军,可以改变割芦苇的方式。
谭玲迪:奥森没有减少割芦苇,因为这是它水体水质的需求,但是你可以按照鸟类和昆虫繁殖的节奏来割芦苇,就比如说春天的时候赶在鸟类繁殖季到来之前,我就把该割的全割了,这样的话,鸟类过来的时候就不会再因为你割芦苇惊扰到它。还有就是有一些蜻蜓,可能它要利用芦苇繁殖,你再适当给它留几小块就行。秋冬的时候你是为了防火的目的需要割芦苇,但是有一些鸟类需要在芦苇丛里面过冬,那就在没有防火风险的地方,比如说水的中间给它留几片。
今年11月,为了冬季防火的需求,奥森割芦苇的工作如期进行。但在此越冬的鸟类并不用担心失去生存的空间。听取山水的建议后,王军决定根据鸟类的习性,每年将割芦苇的次数由1次改为3次,这些变化也给她自己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。
今天,我们环顾北京,印象中满是钢筋水泥的城市,正在被绿色覆盖。持续60多年的防风固沙工程,让北京实现了“由黄到绿”的转变。两轮“百万亩造林”工程,让北京城市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9.29%。但如何让绿“活”起来,是北京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周彩贤:活起来主要是两个意思,一个我们林子造了,量很大,但是我们林子底下光秃秃的,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,不活。另外一个,人进入到森林里面以后,我们感觉到,无所适从就仅仅走走路,人享受森林各种带来的福利还没有,所以人进去也活动不起来。
2017年,北京开始实施第二轮“百万亩造林”,提出了乡土、长寿、抗逆、食源、美观的造林方针,力求通过乡土树种提高抗逆性,并在此基础上为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,恢复生物多样性。
周彩贤:绿了,恢复生态系统。事实上在一个区域一个环境当中,要达到生态系统的平衡,生物必须多样,食物链必须完善,一个物种的灭绝不是代表一个个体,一个链断了,就导致你的生态系统不平衡了。
吕植:城市化的过程,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说,是一个单一化的过程,就变成水泥森林了。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,人强大了以后呢,把我们所依靠的这个生命的基石逐渐摧毁,变得越来越脆弱,越来越不稳定,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强调要保护自然,保护生物多样性,是因为它遇到了危机,实际上是难以为继的。其实自然可以重新来过一遍,而人类不可以。
自然的力量:看见生物的“隐性价值”
北京,一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大都市。许多鸟类、两栖、爬行动物以及植物只要条件适宜,哪怕面积很小也能成为它们的立足之地,与人类聚居区比邻或镶嵌而生。
吕植:北京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潜力是非常大的,但与此同时也是非常脆弱的。所谓的尊重自然,顺应自然,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是其实蛮难的。
位于北京西郊的京西林场,17万亩森林绵延于京西山峦。10月已值深秋,但这里却仍能看到成片的绿色。油松四季常青,在人工山林中极为常见。人们已经很难想象,新中国成立之初,这里也曾“荒山秃岭,风起沙扬。”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,如今已经绿树成荫,但却迎来了新的问题。
安桉:你从卫星一看,一片绿,你走到树林底下其实什么都没有,没有灌木,没有草,光秃秃的一片,我们都管这叫“绿色的荒漠”。
京西林场的前身是京煤集团的企业林场,它的诞生最初是用于煤矿巷道的坑木,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调整,林场成为煤矿企业的一种生态补偿,特定的时代要求决定着像油松、落叶松这样的速生树种都是最佳的选项,但由于林区密度过大而遮蔽了阳光,导致林下的草本植物和灌木都很难生长,这也加剧了物种的单一。
周遵秀:纯林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。因为它没有食物链的循环,没有相互物种的制约和平衡,导致病虫害一旦发生,特别容易扩散蔓延。
事实上,不管是人工林,还是城市中随处可见的人工草坪,都正在经历着从人工化到自然化的转变。
曾经的南门大草坪,是不会有任何动物驻足的。为了维持草坪的四季常青,整齐美观,每年6月底开始,每隔十天就要进行一次打药杀虫。
王军:这个工作是特别程式化的,我有意识地播了一部分蒲公英、紫花地丁,把它变成缀花草坪。当有一定比例其它花卉品种的时候,它的病就不容易蔓延,甚至那块南门大草坪,一年我都不打一次药了,代价是它不是纯冷季型草坪,秋天会黄得早一点,但我一直觉得,其实这个审美也是没有问题的,自然界里头一定是有一年四时变化才是对的。
吕植:我们为什么保护生物多样性呢?是因为多才会稳,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,桌子两条腿立不起来,三条腿能站起来,但是你要是不小心砍掉一条腿它就倒了,如果有十条腿八条腿,它才比较安全。生物多样性越多,生态系统的功能越稳定。
对于京西林场而言,从接管这块林地伊始,就把恢复生物多样性提上了日程,短短几年已经看到了一些可喜的改变。我们来的这天,正赶上修路,一些水泥没干的地方,还可以发现小动物的脚印。
2019年,他们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,开始进行“开林窗”尝试,通过疏伐,为林下植被生长创造阳光和空间条件,用这种方法来恢复生态。用他们的话讲,不是所有树木都叫森林,有时候砍树比植树更能帮助森林恢复到自然健康的状态。
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树苗,让周遵秀她们欣喜不已,作为外行人可能无法理解,它们对于这个生态系统意味着什么。
周遵秀:比如说栎类,顶级生物群落的一个指示物种,今年咱们看到的可能好多都是小苗,可能20年以后,它能长成这种大树,稳定的生态群落就已经构成了。
原始森林中,动物植物微生物在这个大环境中各司其职,维持着稳定与和谐。对于植物而言,它们需要借助大自然的帮助,才能将种子和幼苗传递到森林的各个角落,换句话讲,昆虫,鸟类都是它生生不息的依赖。
郭耕:一般人说520就是我爱你,但(那天)也是国际蜜蜂日。一千三百多种作物,有一千种以上都依赖蜂类来传播花粉。如果没有蜜蜂了,我们的农业、畜牧业、水果、蔬菜都会减产,都会遭到损失。人类往往看到的是直接的价值,是产品价值,但是它们还有更多的生命支撑价值,这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价值。
城市的未来:留野、保育,从生物的视角出发
2017年,北京市决定,在城市中心区东北部,朝阳、昌平、顺义三区交界,温榆河、清河两河交汇之处,规划建造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的温榆河公园。
因公园位置地处三区河道交界,同时也是北京重要的蓄滞洪区,温榆河公园的筹划建设,最终由北京市水务局进行牵头,并于2019年成立了北京市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。
李文宇:其实刚开始就是以防洪功能为主,但是它又特别大,不一定30平方公里全部去建蓄滞洪区。我们测算过周边大概有上百万居民,其实也是为了给这些市民提供体验生态自然这么一个大的空间。
温榆河一期工程在2020年9月正式对市民开放。随即迅速成为周边居民踏青、露营的最佳选择。在满足人需求的同时,园内遍布芦苇湿地,并无水泥硬化的滩涂、沿河没有封闭的水域廊道、乔灌草相互结合的空间规划,这些都是考虑到野生动物而进行的设计。
“生境”,意为生物生活的生态地理环境。这是温榆河公园设计规划中被反复提及的词语。在园林设计师王贤看来,30平方公里的范围已经远超公园的尺度,温榆河公园的设计、建设究竟该以何为本?这是他一直困扰的问题。
王贤:温榆河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城市建设区,也不是(类似)三江源生物保护区,中间的这个区域我们如何去界定它的优先级,当时围绕到底是考虑人,还是优先考虑动物,有很多的争论。
在以生态为本的前提下,北京市决定采纳吕植教授提出的“留野”概念。目前,“留野”已成为北京市园林绿化管理的基本要求之一。
吕植:所谓“留野”就是让它自己长,不要再去割它,去管它,再去种它,让它自己演化,让自然做自然的事情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,人来帮助营造一个自然场景也是可以的,但前提是我们了解自然是什么样子,这些生物需要什么,需要的是草,不是树,需要的是湿地,或者是滩涂。
在温榆河公园的最终设计方案中,我们看到了一心、三核、四脉的自然带空间格局,整个公园的“留野”范围占据公园总面积的30%,为各种生物提供与之适应的生境。
如今,北京的本土植物,越来越成为园林绿化工作者的首选。2020年以来,北京市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,生物学家们的足迹遍布山野,实地了解最新动向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数据显示,北京地区目前已有记录维管束植物2088种,其中国家及北京市重点保护植物80种。而除此之外,还有近600种陆生脊椎野生动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栖息繁衍。
按照规划,北京每年要在园区、校区、社区等场所建设120处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区,为小动物营造栖息地。类似昆虫窝、刺猬屋、蚯蚓塔等一系列为小动物服务的设施就出现在人们身边。
夏舫:以前我们做绿化是绿起来就好,后来就变成不光要绿,还要美,现在我们是让它活起来,物种的多样性让它更多,更丰富。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方方面面,我在大的园区当中要实现那样的一个目标,那我在小的社区当中,实现的目标是不一样的,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增强人的一种保护意识。
夏主任告诉我们,在小区中有一棵柿子树,而每当丰收时节,物业提醒业主来收果子的时候,业主却说,这些果子就让它留在树上吧,它们本来就是为鸟而留的。
奥森公园里的鸟楼,是王军每天早上巡视公园都要来的地方,鸟楼的700多个房间,入住率达到了8成以上。
王军:建奥森的时候,它那个设计理念还是比较先进的,城市生态公园,多多少少还是考虑到了鸟类,这种近自然的环境其实现在看起来,这个路子还是挺对的。
当城市快速发展,许多小孩的童年也随之被钢筋水泥的“森林”围困住,他们或许了解最新的科技产品,精通琴棋书画,但对身边家园,身边的一草一木知之甚少。随着近年来户外运动的频繁“出圈”,人们越来越意识到,大自然给予的不仅仅是快乐,还有更多有趣的知识吸引着他们去探索。